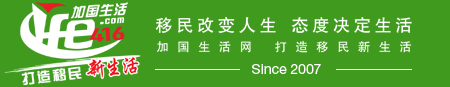前些日子,我曾大连某超市买了几只香瓜,拿回家切开吃,发觉不仅吃着瓜瓤不甜,而且闻着也没香味,可谓“名不符实”。这个时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乡上海浦东三林塘吃的崩瓜,香甜而多汁,那才真叫绝,岂是眼前的香瓜可比。可惜,我有几十多年没有吃到崩瓜了,每当想起它,我的思绪就会回溯到少年时代……
▲我在大连某超市购买的香瓜

▲家乡三林塘的特产“崩瓜”(摘自网络)
那年,还在上初二,一次偶然机会,我才对家乡特产“崩瓜”有所了解。
这事要从我的三舅妈讲起。那个年代,三林塘镇上家庭分为“居民户”和“农民户”,我三舅在浙江某企业工作,而三舅妈却是农民户口,所以,她经常要参加生活队的劳动。由于我从小得到三舅妈的关爱,所以,我对她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那年,她正怀着孕,我就承担了她所不能干的重活,如去水桥头挑水,洗被单等。有一天,生产队轮到她与另一位队员晚上共同去守望瓜田,我忘了当时是三舅妈让我去、还是我主动要求替代她去干这个活。
巧的是,当晚的另一位守望人也是对门邻居,他是我二舅母的小弟,年纪只比我大五六岁,从辈分上我得叫他娘舅。在当地,经常将自己多位舅舅姓名的后位字添加在“娘舅”前,如我的三个舅舅姓名第二个字分别为“德”、“志”和“方”,我就分别叫他们为“德娘舅”、“志娘舅”和“方娘舅”,而这位舅舅的姓名后位字只有一个“然”字,由于他的岁数与我差不多,平时不分什么辈分,所以常直呼他名字,但在人多场合还是尊称他为“然娘舅”。
然娘舅家也是农民户,他没读几年书,年纪很小就到农田干活了。由于他有口吃的毛病,故镇上有些人经常拿他开玩笑。但我从不讥笑他,加上还有亲戚、邻居关系,所以他跟我家的关系很近,经常到我家里来串门。周日时,他邀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起到十几公里远的周浦镇玩,请我在那里小吃店吃馄饨和生煎包等。一开始我年纪小,只配坐在他车后座上,到初中时,我人长高了,而且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就让他坐在车后面,由我踏车带他去玩。如果说他是我生活中的长辈,还不如说他是我少年时的好伙伴。
话说那天晚上,我与然娘舅一起来到瓜田,瓜田的面积很大,一面紧靠一条小河,另一面就是广阔的瓜田。在小河边搭有一个小茅棚,供看瓜人休息避雨之用。那天天晴,明月当空,我就与然娘舅坐在小河边守望。然娘舅说:“生产队里有规定,看瓜人可以随便吃瓜,但不许带回家”。说完,他去选摘了几个瓜,在河水里洗了洗,递给我时又说“这种瓜皮很薄,不用刀切,用拳头轻轻一敲,它就裂开了,你试试看”。我接过瓜来,看那瓜呈椭圆形,瓜的表皮有网纹。按照然娘舅的方法,用拳头轻轻一敲,果真瓜就裂开了,看瓜瓤呈菊黄色,嵌棕红色瓜子,瓜肉进嘴里汁多浓郁,又甜又香,真好吃极了。
然娘舅告诉我:“”这瓜是我们三林塘的特产,名叫“崩瓜”,为啥这样叫呢?大概就是轻轻一敲它就会崩裂的原因”。后来,我还听说,这种瓜到了成熟期,即使人走过瓜田稍重的脚步声,也会使它崩裂。而上海话念“崩”字音为“浜”,故也有人把此瓜写成“浜瓜”。
我与然娘舅吃够了,就一起坐在小河边草地上聊天。此时,天上星星就在头顶闪烁,小河哗哗就在脚下流淌,蟋蟀青蛙叫声在周围此起彼伏,我俩好象置身在一个动画般的世界。然娘舅问我:“你待在这里不觉得害怕吗?”,我说“有你然娘舅在我怕什么?”他笑了,觉得与我在一起他是长者,很自豪。他说:“你这样爱吃崩瓜,只要我在种田,就保证你常能吃到”,我也笑了,觉得得到他的关爱,很舒心。他又问我:“以后你读书后会不会离开三林塘?”,我说:“我也不知道”,此时,我俩都沉默了,这句话好象有预言,今后的我远远离开了家乡,一辈子在东北定居生活。
自我与然娘舅一起守望几天瓜田后,就经常吃到他留给我的崩瓜,他是把这件事记在了心头。时间过得很快。十九岁那年我考上大学。要远离生我养我的家乡了,然娘舅很是不舍得我走,不知从那里找来一本学生用的地图册,要我指给他看大连在中国的哪个位置上,他说:“到了那里可吃不到崩瓜了”,听他讲此话,我的心里不禁一阵心酸。临走那天,他骑自行车把我的行李一直送到公平路码头。后来到船上我才发现,在网线兜的脸盆里,他又塞进了几只崩瓜,我明白是让带到船上吃的,这甜香的瓜儿伴随着我渡过远洋。
我大一时放暑假回家,正巧遇到然娘舅娶亲,我与老同学JQ还一起到我家隔壁二楼新房上去看新娘。新娘长得很漂亮,家在无锡某地农村,年龄比我还小一二岁,但论辈分我还得叫她舅妈。这一次回家他没有时间陪我玩了,也没吃到他送的崩瓜,但吃到了喜糖。我非常理解他办喜事时的忙碌,也为他能娶到这样一位漂亮老婆而感到高兴。
光阴似箭,大学五年级时,我遭受到一次车祸,左腿受伤,在医院治疗后,学校安排老师把我送回老家休养。当远洋轮停靠上海公平路码头,然娘舅出现在船舱里,原来他奉我母亲之命来接我回家。他背着我吃力地爬上陡峭的船梯,我卧在他的背上,头依在他头颅一侧,望着他额头渗出的汗珠,我流泪了,泪水滴落在他的肩膀上。来到船码头,只见那里停放着一辆当地生产队常用的送菜拖车(脚踏三轮车),车上装着一张躺椅,然娘舅把我安放在上面,他流着大汗踏了几十公里路一直拉到家里。这段恩情令我永世不忘,写到这里,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
在家里休养的日子里,我与然娘舅又能够经常相处一起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添有一个儿子,成了我俩嬉戏的好“玩具”。这段日子里,我又没少吃他家自留地里种的崩瓜,吃瓜时,我俩又回忆起当年守望瓜田的时刻,感叹人生之变化。后来,我恢复健康后,返回大连后被学校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那个时候,通信联络主要是靠写信,我在写家信时,经常要带上一句“代向然娘舅问好”的字样。每次回家探亲,我都要带一大箱苹果回沪,第一个分配对象就是然娘舅,当我将苹果送到他面前时,我总会开玩笑说:“是苹果甜还是崩瓜甜?”,这句话一讲,我俩会哈哈大笑,其实我俩心中都明白,只有家乡的崩瓜才是最甜的。
时间过得很快,二十几年过去,然娘舅夫妇生养的两个儿子也长大成人,他俩开始忙乎为儿子成家盖新房,而他们自己仍住在老旧房子里。有一年回家,然娘舅领我到他新开的小吃店吃小馄饨,他老婆也知道我俩的关系,下了满满一大碗,我边吃边与他讲小时候到周浦镇吃馄饨的情景,我还讲起他从未去外地旅游,诚恳地邀请他夫妻一起到大连来玩,他俩也答应了,约定有机会一定去。后来听说他俩将小吃店关了,由于三林镇附近的菜田大都被征用,他又去一家钢管厂打工。随着三林镇部分住宅拆迁,我父母和然娘舅的家也分别从三林老镇原居住地各自搬迁到另外地方,时间长了,连我妈妈也难得到然娘舅他家的信息了。
三年前的一次回家探亲,我妹妹告诉我一个惊天消息:然娘舅因患肝癌去世,享年只有六十几岁。我伤心极了,特意去拆迁的地方悼念他,我站在三鲁桥上,面对着三林江水,一遍遍呼唤然娘舅的名字。正巧他的一位侄女骑车经过,看到我在桥上,就跟我讲起然娘舅得病时的情况,听说他病重时,连声呼唤他的儿子救救他。我知道,他是多么的热爱生活,更何况我俩的约定还没实现,怎么能想到这么快就离我而去呢?更令人难以想象的,随着三林镇附近菜田的征用,早年的瓜田早就被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所占领,我回去都分不清东西南北。当然,富含着我与然娘舅情感的崩瓜也随着他一起在人世间消失了……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上海《新闻晨报》一篇报道,文章里说:被称为西瓜一绝的三林崩瓜在失传30余年后又重新回归了。昨日,记者在浦东三林镇举办的“三林崩瓜暨端午民俗活动周”上获悉,今年三林崩瓜将首次进入市区大型超市,因为种植难度大导致市场总体供应量并不会太多,均价估计8元一斤。获知此消息,我的心中甚感欣慰,愿然娘舅在天之灵保佑浸透着我俩深厚情谊的家乡特产“崩瓜”会永世传承。
(完) ——写于2011年6月8日